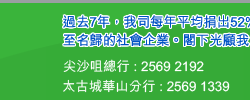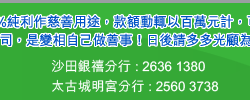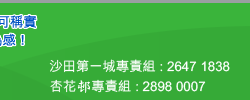從去年開始,我有一位朋友一心培養我在京劇中的興趣,所以在我每次去北京期間,他都會請我去看京劇,也是通過他,我結識了不少的京劇界的朋友。在港澳我們基本上是不可能在現場欣賞到京劇藝術。所以我的很多京劇界的朋友們都推薦我看中央電視臺的戲曲頻道,雖然在戲曲頻道上也有各種不同的其他地方戲曲,但這個頻道的節目還是以京劇為主的。我以前寫文章時經常聽著歌劇。但在最近好幾個月裡,我會在電視機播報新聞後,將電視台轉到戲曲頻道收聽京劇。我發覺經過幾個月後,我也已習慣聽戲曲頻道裡播放的京劇。而且我越來越覺得京劇的音韻也非常悅耳。一邊寫文章一邊欣賞著京劇藝術家們的演唱的感覺,和我在聽歌劇時是幾乎差不多的。它們都能令我在心情愉快的情況下書寫流暢。
有一次當我正在聽著京劇並寫著文章時,發現自己有些疲倦的感覺,因此停下筆來,伸了個懶腰。在過程中不經意地轉身看到電視臺中正在播放的京劇。突然我發現在電視螢幕上的京劇藝術家們的手都是黑色的。在開始時我還以為可能是自己的眼睛有問題或者是舞臺上燈光的問題。但是我揉了揉眼睛,仔細地注視螢光幕上藝術家們的手。我發覺我看到是事實。這絕對不是我眼睛出現了問題,也不是我的錯覺,更不是舞臺燈光的問題。藝術家們的手的顏色和他們戲服雪白的水袖顏色黑白分明,給人一種特別奇怪的感覺。他們的手的顏色和他們臉的顏色也是全然不同的,看起來就好像一個白種人或黃種人生了一對黑種人的手。我對舞臺上出現這種情況感到奇怪,也覺得好笑。我問自己這是為什麼,這正常嗎?我緊緊地盯著螢光幕留意地注視了臺上每個演員的手。突然我明白了這種情況的出現是因為演員們將臉化妝了、塗白了,但是他們卻沒有將手也塗白,也因此他們的手的顏色和臉的顏色出現了很大的差別,這種差別在強烈的燈光下就顯得格外地突出。
從那天以後,我每次看中央臺的戲曲臺時,就會特別地注意看劇中藝術家們的手。令我驚奇的是這種現象普遍存在。而手和臉同色的演員雖然也有,但卻只屬少數。這樣的現象連續不斷地在電視機中出現令我感到很不安、也很反感。在我這個外行人看來,這並非一個不可克服的難題,但令我不能相信的是被稱為國萃的京劇藝術中,竟然重複不斷地長期地存在著這麼一個不應存在的瑕疵。當然演員手的顏色並不影響演員們的唱功、做功。對整部戲劇來說,也可能只是一個再小不過和無關緊要的細節。但是那對黑色的手,破壞了像我這樣的外行觀衆心目中在欣賞京劇時對舞臺上美的觀感的追求。對我來說,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細節,而且這樣的錯誤根本不應該出現。因為從這種小地方最能看出人在辦事時,是否真正的專業、認真和負責任。
我一直認為外國經典歌劇是美聲和音樂融合後,出現在這個世界上最能引起人們心靈共鳴的聲音。也因此,我們只要用我們的耳朶就可以感受到它的優美。我們可以不親臨劇院,而只僅僅依靠音響就能達到我們心靈上對音樂的感應和共鳴。而我們的京劇除了藝術家們唱得可以令人陶醉外,在現場看藝術家們在舞臺上的出色表演,更是上好的享受。藝術家們在一抬手、一踢腿中都能帶給觀衆優美無比的觀感享受。在表演藝術層面上,我個人認為,我們的國萃京劇絕對比外國經典歌劇更勝一籌,但是當我看到藝術家們伸出“黑爪子”時,心裡真的大叫“煞風景”。我問為什麼面對成千上萬觀衆的戲曲臺裡,竟然讓這樣的錯誤不斷地出現?我搖頭、嘆息、難道這是我又一次犯了吹毛求疵的毛病?.......
我的同事和親友們經常說我過於執著,也過於追求完美。他們說得一點都沒錯。我在工作時的確是真的六親不認的。而且我也特別注意細節,哪怕是在不傷大雅的小事上,我都不容馬虎。所以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往往會覺得特別的辛苦。他們也常常會特別地小心翼翼,生怕在一個不小心時出了個無心錯而遭到我的責備。其實剛接觸我的和剛開始和我共事的人,可能會對我的工作方式和要求嚴格感到不習慣,有的甚至會覺得我吹毛求疵。但是和我相處時間長久以後,當他們習慣了我的工作要求和作風後,絕大部分人都會認同我,並像我一樣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要求把事情做得最完美。因為大家的心中都明白,小的錯誤是很容易糾正的,問題是我們是否真心想把我們的工作做得最好。
在不久前,我有一次遇到立法會秘書處的處長Erica和科長Lucia。Lucia笑著告訴我,她的上司Erica在佈置工作後不到3分鐘,就會打電話催工作完成了沒有?弄得秘書處工作人員都特別緊張。而處長Erica也笑著說,她在我任立法會主席時,在我辦公室門口坐了差不多十年時間(Erica本來是立法會執行委員會的協調員,直接由我領導和分配工作,到我快卸任時才調去秘書處任處長)。她在不知不覺中養成了追求高效率的工作習慣。現在她已容不得慢吞吞的工作作風。她還告訴我在剛開始為我做事時,她常常提心吊膽、手足無措。和我相處長達14年的前秘書Alice在我離開立法會後曾說:“可能跟隨你的日子太長了,很多事已成為習慣,習慣一旦改變,總是比較難以適應,而我的性格某程度上也因你而改變了”。
寫到這裡,我的腦中出現了曾任我秘書和助理長達20年的Celeste。Celeste是我第一位正式的秘書,她從19歲就來我身邊工作。Celeste曾伴隨和見證我一生中事業的建立和發展的過程。她聰明、好學、勤奮並任勞任怨。我和她的關係在她因移民離開澳門時已十分親密。在她離開後,我對她的思念也一直特別的強烈和從未間斷。但是在開始時,Celeste和我也有一段不短的工作方式、方法和相處的磨合期。70年代時的科技落後,我們辦公室用的打字機都是很巨大和舊式的。那時的打字機的鍵盤都特別的笨重。在澳葡時期給政府發公函都要用政府規定的橫格藍色稟紙。而且必須用葡文書寫。Celeste從未學過葡文,所以我心知肚明要她用葡文打字,已經很難為她了。而由於打字機的鍵盤笨重,只要手指用力稍有不均,就會出現字體顏色深淺不勻或上下錯位的情況。但每次當Celeste將出現字體顏色深淺不勻或上下錯位的稟紙拿來給我簽字時,我都拒絕接受,而且每次要退回給她重新打字。我記得開始時,Celeste會被我氣得一邊留淚一邊打字。她就這樣一遍一遍的重複加班打字,直到我滿意收工為止。當然我也常常對她心存歉意,但我一直還是堅持這樣做。我告訴她,我知道她辛苦,但是我不著急,我可以等到她順利完成任務才走。我還告訴她,如果我不在一開始就堅持的話,她是不會進步的。另外我告訴她,我們給政府的公函,代表的是公司的形象,一份連打字和格式都不像樣的信件,反映的是公司管理不善,會給人留下壞的印象。是對收信人的不尊重,也是對我們自己不尊重的表現。當然在她加班的情況下,我會坐在辦公室等她把完美無瑕的文件拿給我簽署後,才和她一起離開辦公室而回家。在我的嚴格的要求和她的努力下,Celeste進步神速,到後期只要經過Celeste手的文件,我根本不用再看,因為凡是經Celeste手的文件都是不會存在任何瑕疵的。我記得澳門葡籍大律師華年達曾告訴我,Celeste是他見過的一位最好的秘書和助手。
在我到澳門初期,根本不懂管理、不會做生意,更加不知道毛衫生產是怎麼回事。另外我大學畢業後,匆匆忙忙地讀了不到一年的英文,所以英文程度實在有限。當然在那個時候,我是從來未見過英文的商業信件,所以公司裡的一切對我來說都是沒有接觸過的東西。幸虧當時年輕,所以心中沒有“害怕、膽怯”這四個字。不會做的要做,不懂的也要懂,每天就這樣的過著“摸著石頭過河”的日子。有一次,我必須寫一封英文信給澳門大西洋銀行的信貸部。在那個時期寫中文商業信對我來說已屬非常困難,寫英文信那就更是難上加難。所以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寫好了信,簽署以後將信送去了銀行。兩個小時後,我收到大西洋銀行信貸部的一位葡籍土生打來的電話,在電話中,他將我臭駡了一頓,他說我如果還沒有學會寫信的話,回學校學好了再出來做事。並要我立刻派人將那封“狗屁不通”的信件拿回公司。他直斥我的無能,他說他不相信像我這樣的“經理”能將公司管理好。我在他臭駡我時,趕緊拿出信件複印本,一看之下,我自己也給嚇儍了,因為打字員(當時Celeste尚未來我公司工作)在信件中整整漏了一段。那的確是一封牛頭不對馬嘴且令人無法明白的信件。當然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除了賠禮道歉外,一句嘴都不敢駁。但這件事除了令我留下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象外,對我的刺激也特別大。我從那天起一直將這件事牢記心頭,也不容在我的工作中再次出現這樣的錯誤。另外,我為提高我的英文水準,而報讀了英國一間大學的商業英語函授課程。其實我雖然從此不大敢面對這位土生葡人,但心中對他卻是十分地感激。他的一頓駡,雖然大大地打擊了我的自尊心,但是他的駡也促使我發奮上進。我除了報讀了商業英語函授課程外,還先後報讀了企業管理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函授課程。另外,我對自己和同事們在工作上的要求也從此特別地嚴格了。
當我寫到這裡時,我覺得有些疲倦。我關掉唱機,打開了電視機。中央臺的戲曲臺正好在播放中國京劇音配像的“得意緣”。這齣戲是我連名字都沒聽過的戲,本來我是很有興趣收看它的。但我再次看到了令我胃口大倒的一雙雙“黑爪子”。在那一刻我禁不住自問,是我這個外行人的“吹毛求疵”在作怪,還是藝術家們忘掉了他們應有的忠於藝術的職業精神。